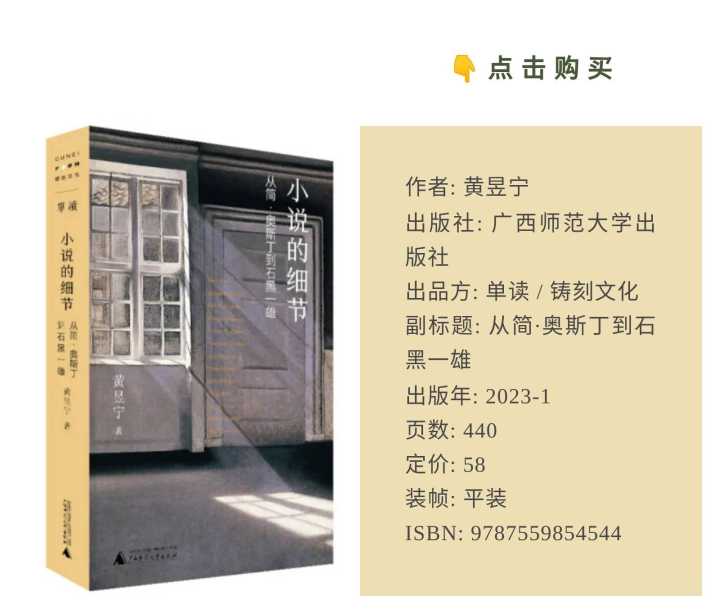
麦克尤恩2018年访华时,白天宣传他以前写的小说,晚上被时差折磨得难以入睡时,就看他刚刚写完的书稿——《我这样的机器》,男主角是个机器人。我听他讲故事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但改动了关键的时代变量:英国在福岛战役(福岛又称马岛)中输给了阿根廷,撒切尔夫人提前下台,图灵没有自杀,反而一举提升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于是可以乱真的家政机器人在1980年代就进入了消费市场……这个把未来嵌入过去的设定,让我想起石黑一雄在《莫失莫忘》里也把专供器官移植的克隆人拉进了1970年代的背景。我向麦老师提起这本书,他一脸茫然:“我好像记得这电影……但我在写这本书时完全没想到它,是的,我确定我没有想过。”
石黑一雄还在写《克拉拉与太阳》时,好朋友麦克尤恩刚刚出版了《我这样的机器》。他知道,这两本书的题材都与人工智能有关。在石黑自己完工之前,他刻意避开一切能读到《我这样的机器》的机会——他要抵抗任何有可能让他的克拉拉“变质”的可能。表面上,克拉拉和亚当确实都有相似的人设,都是那种兼具服务与陪伴功能的机器人。不过,只要你把这两本书全部看完,就能完全确定,克拉拉与亚当并没有撞型的危险——正如石黑一雄和麦克尤恩,他们就算是一个被另一个捏住了握笔的手,也永远不可能写成对方的那种样子。
* * *
这是看到了希望的宗教渴求,这是科学界的圣杯。我们雄心万丈——要实现一个创世的神话,要办一件可怖的大事,彰显我们对自己的爱。一旦条件许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听从我们的欲望,置一切后果于不顾。用最高尚的言辞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摆脱凡人属性,挑战造物之神,甚至用一个完美无瑕的自我取而代之。说得实际一点,我们要给自己设计一个更完善、更现代的版本,享受发明的喜悦感和掌控的激动感,二十世纪入秋之际,这终于成为现实,我们迈出了第一步,从此一个古老梦想的实现可以期许,从此我们将开始那漫长的功课,逐渐认识到,虽然我们非常复杂,虽然我们哪怕最简单的行为和生存模式都无法轻易地正确描述,但是我们会被模仿,会被超越。而且,那时候我在场,还是个年轻人,在那料峭的拂晓时分,正急不可耐地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这样的机器》
罗莎和我新来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商店中区,靠近杂志桌的那一侧,视线可以透过大半扇窗户。因此我们能够看着外面——行色匆匆的办公室工人、出租车、跑步者、游客、乞丐和他的狗、RPO大楼的下半截。等到我们适应了环境,经理便允许我们走到店面前头,一直走到橱窗背后,这时我们才看到RPO大楼究竟有多高。如果我们过去的时机凑巧,我们便能看到太阳在赶路,在一栋栋大楼的楼顶之间穿行,从我们这一侧穿到RPO大楼的那一侧。
——《克拉拉与太阳》第一部
这是两部小说的开头。麦克尤恩笔下的“我”,是虚拟的上世纪80年代里的首批智能机器人用户,雄心勃勃的宣言里显然洋溢着反讽意味;石黑一雄笔下的“我”,则正好是那个“古老梦想”的对象。这位叙述者名叫克拉拉,我们跟着她的叙述获得了从商店橱窗里向外望的独特视角。我们很快就可以推断,克拉拉并不是在橱窗里忙碌的工作人员,而是被陈列在橱窗里——没错,克拉拉虽然在用平实的语言、平静的语气在跟我们讲故事,可她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橱窗里的一件商品。
从一开始,克拉拉就提醒我们注意她看待太阳的独特方式。她在橱窗里看着太阳在外面赶路,还尽可能把脸伸过去,好接受太阳的滋养,为此引起同伴的抗议,说她总想把太阳据为己有。我们由此可推断出,克拉拉和她的同伴都是依靠太阳能维持生命运转的机器人,他们陈列在橱窗里供人观看、选购,为人们提供服务。这些机器人有个统一的型号,叫AF。AF更新的速度很快,我们读到后面几章就会发现,克拉拉是第四代AF,也就是所谓B2型的。比起刚刚上架的第五代B3来,克拉拉和她的同伴们似乎已经有了滞销的趋势,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小说写得很慢。我们耐下性子,细细咀嚼,才能感觉出越来越多的异样。到橱窗跟前来挑选的大部分都是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可见AF的设计定位就是儿童的成长伙伴,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孩子释放负能量的渠道和工具。经理灌输给克拉拉的理念充满了善良、慈悲和同理心,她说:“如果有时候一个孩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带着怨恨或悲伤,透过玻璃说一些让人不愉快的话,你不要多想。你只需记住:一个那样的孩子很可能是满心沮丧的。”不过,克拉拉透过橱窗看到的世界却无法用经理说的那些真善美的道理来解释,她看到有的孩子对他的AF很粗暴,有的孩子并不需要陪伴,她还看到大人们在马路上暴力相向,在她眼里,这些大人们“打起架来,就好像世上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多地伤害彼此”。
克拉拉在橱窗里陈列了四天之后,一个叫乔西的少女走进了她的世界。乔西看起来很聪明,打第一眼照面就喜欢上了克拉拉,但是克拉拉从她的步态里就能看出乔西的身体很羸弱,而且她母亲的态度暧昧不明,似乎选购这个机器人不仅仅是为了哄女儿高兴,这个计划里仿佛藏着什么秘密,而母亲对此欲言又止。几经犹豫,在乔西的一再坚持下,母女俩终于把克拉拉买回了家。
* * *
母亲朝我探过身来,身体越过桌面,眼睛眯了起来,直到她的脸庞占满了八格空间,只留下边缘的几格给瀑布;有那么一刻,我感觉她的表情在不同的方格间变化不定。在一格中,譬如说,她的眼睛在残酷地笑着,而在下一格中,这双眼里又满是伤悲。瀑布、孩子和狗的声音全都渐次消逝,直至缄默,为母亲将要道出的话让路。
——《克拉拉与太阳》第二部
在乔西家,克拉拉就如同生活在一团精致的迷雾中。表面上看,尽管乔西的父母早已离婚,但家里生活富足,母女关系和谐,一切都是幸福的中产阶级生活该有的样子。然而,克拉拉从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蛛丝马迹。首先,乔西与邻居的孩子里克青梅竹马,就像《呼啸山庄》里的卡瑟琳和希克厉那样从小立下誓言要永远在一起,但里克似乎并不属于乔西的生活圈层,他的母亲认为他绝无可能考上乔西要去的那所名校;其次,我们发现,他们之间之所以会有这样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母亲曾经做过截然不同的选择:乔西从小经历过一种叫作“提升”(lifted)的程序,改善优化了她的基因,而里克却没有;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提升”的过程其实是存在风险的,而乔西的身体就承受了“提升”带来的巨大代价,她的健康受到了损害,正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事实上,乔西的姐姐萨尔,当年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病入膏肓,几年前就已经不治身亡了。对此,母亲一直讳莫如深。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进展到这里,所有这些线索都是我们透过克拉拉的叙述推断出来的。直到小说结束,克拉拉也不交代具体的时间地点。她把眼前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对于事物之间的深层关系或是语焉不详,或是点到即止。克拉拉恪守机器人的视角,给我们的阅读造成了大量留白。我们能感知到的是,这并不是描写当下现实的小说,它显然具有某些科幻小说的元素。但与一般科幻小说不同的是,它几乎没有在交代时空背景、解释科学道理、构建世界观框架上耗费笔墨。同样石黑也不会像麦克尤恩那样,精心设计机关,描述亚当如何迅速玩转人类的智力游戏,如何用他美好的初衷将他的主人一步步逼到尴尬的境地。一如既往,我们看着麦克尤恩凭着他强大的逻辑和丰富的背景知识直奔“麦克尤恩瞬间”。石黑一雄完全是另一种写法。直到读完《克拉拉与太阳》,我们仍然对这个特定时空所达到的人工智能水平,对于所谓“提升”是一种怎样的过程,没有清晰的科学概念。“提升”为什么会造成乔西姐妹的疾病,“提升”技术与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制造污染的“库廷斯机器”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部小说都没有完整的解释。我们只能通过克拉拉断断续续的叙述,大致构建出自己的猜测。
我们在《莫失莫忘》里接触过相似的配方。石黑在处理《莫失莫忘》的时候同样将科技因素淡化到极致,科幻元素只负责提供简单的设定。石黑真正关心的是在这样的黑暗设定下,这些克隆人如何从懵懂到醒悟,如何从无忧无虑到直面命运的诅咒。不过,这部小说更动人的地方在于,令人恐惧和悲伤的设定与平凡琐碎甚至优美的现实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小说中用了大量缓慢而诗意的笔墨,耐心描写囚禁克隆人的寄宿学校里的日常生活,与残酷的真相形成令人震惊的对照。詹姆斯·伍德将这些优美的描写形容成“淡金色的散文”,并且解释了这样写的妙处。伍德说:“这部小说将科幻叙事穿插在真实世界的肋骨缝之间,让它在呼吸中吐出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继而将科幻小说转向,反过来安置在人类身上,让它在恐怖的同时流露出平凡的感人气息。”也就是说,写克隆人的生活和感受,最终还是为了用他们的故事来隐喻人类自己的问题,当我们不由自主地代入克隆人的叙述时,他们的无助也就成了我们的无助。
我们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尤其是前半部分里同样能读到这种“淡金色的散文”。无论是克拉拉在橱窗里看街景上的人世百态,还是到乔西家里不紧不慢地观察环境、推断人物关系,都写得那么生活化,节奏如田园诗一般舒缓而优美,间或才有恐惧和不祥的微风一丝丝渗进来。耐人寻味的是,克拉拉被人类预设的参数显然都是人们自己从来没达到的道德标准,比如善良、无私、强大的共情能力,因此克拉拉虽然对身边观察得事无巨细,但她对人们言行的判断却始终充满善意,对于任何人任何事都能看到好的一面。不过,克拉拉的视觉跟人类不同,所有景物在她眼中是分成一格一格的。有时她眼中的画面会出现奇特的分裂,而这往往与画面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有关。比如,当乔西的母亲故意找到与克拉拉单独相处的机会,要求克拉拉模仿乔西、“扮演”乔西时,克拉拉眼中的母亲的形象就会发生裂变。
小说没有交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裂画面——与之对应的是人格的分裂,还是对他人以及自我的欺骗?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母亲当初把克拉拉带回家,不仅仅是为了陪伴病重的乔西。果然,此后小说的叙事节奏开始加快,此前埋下的各种若隐若现的矛盾终于浮出水面,并且纠缠在一起,而克拉拉成为这一切冲突的旁观者和参与者。当年是否参与“提升”,成为今日所有痛苦的根源。绝望的母亲把克拉拉当成了救命稻草,想让“高仿”的乔西的皮囊与智能机器人克拉拉合成一个乔西的替代品,用来“延续”乔西的生命。
小说最具有哲学性、最有思考空间的部分就在这里。替代项目的主导者卡帕尔迪先生振振有词,声称在人工智能发展到高级阶段,每个人的内核深处并没有什么独一无二、不能复制的东西,他实际上等于否定了人的精神层面的主体性和独立价值,将“万物之灵”分解为一连串数字编码。这种看起来有理有据的论调甚至对一向反对延续计划的乔西的父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对克拉拉说:“我想,我之所以恨卡帕尔迪,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怀疑他也许是对的。怀疑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怀疑如今科学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我女儿身上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东西,任何我们的现代工具无法发掘、复制、转移的东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父亲的激烈反对,除了出于对女儿乔西的爱,实际上更大的动力在于捍卫自己对人类这个物种的信念。问题在于,当一种信念需要激烈捍卫时,恰恰说明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事情到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相当吊诡的局面。围绕在乔西身边的人们,都在痛苦而热烈地讨论着乔西能不能被延续、人类能不能被复制,众人的潜台词都是对乔西的康复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实际上已经完全放弃了乔西。只有一个人没有放弃——她甚至不能被称为人。只有机器人克拉拉还在千方百计地思考怎样摧毁造成环境污染的库廷斯机器,怎样拯救乔西。
最终的解决方案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我们不妨把这个小小的悬念留下来。可以略微提示读者注意的是,解开这个悬念的钥匙就藏在小说的标题——克拉拉与太阳——中。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麦克尤恩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但它一旦出现在石黑一雄“淡金色的散文”中,却又显得那么贴切自然。
* * *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个可能打动他的理由了。我说:“拜托,我们想想玛丽娅姆。戈林对她做过什么,又产生了什么后果。米兰达只有撒谎才能得到正义。可是,真相并不总是一切啊。”
亚当疑惑地看着我。“这话说得可不同一般。真相当然就是一切啊。”
米兰达疲倦地说:“我知道你会改变主意的。”
亚当说:“恐怕不会。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复仇,还是法治。选择很简单。”
——《我这样的机器》
这是典型的麦克尤恩式的写法。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堆积,越来越尖锐,人物的怒火像麻花一样渐渐拧在一起,事件即将迎来爆发的戏剧瞬间。在石黑一雄这里,人物从迷雾中走来,又消失在迷雾中;换作麦克尤恩,人物的“疲倦”常常意味着不可思议的一跃而起。
在机器人亚当看来,世界是非黑即白的,正义是绝对的,真相就是一切。当他质问主人“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时,他的答案是唯一的:世界应该符合人类对他的出厂设定——那是设计者怀着对世界的美好愿望,输入的至美至善至真的道德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亚当当然不会像克拉拉那样忍耐人们的虚伪与善变,也不会在混沌的现实中默默地等待拨云见日,像美人鱼那样恰到好处地出现或者消失在人们需要她的地方。亚当自以为能拯救人类的方式就是不回避也不妥协,一条道跑到黑。当他自说自话地把替男主人挣的钱普济天下时,当他执着地要把女主人推向被告席时,机器人亚当的悲剧,那个属于他的“麦克尤恩瞬间”,也就无可避免了。
借此,麦克尤恩再次把尖锐的笔触径直刺入核心——亚当的困境说到底是人类自己的困境。最能代表作者立场的是小说中那个在平行世界里并没有自杀、反而靠人工智能发了大财的图灵的总结性发言:“他们不理解我们,因为我们不理解自己。他们的学习程序无法处理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大脑,那我们怎么能设计他们的大脑,还指望他们与我们一起能够幸福呢?”
唯有在一个问题上,克拉拉和亚当是同一类(机器)人——他们的最高理想都是无限接近人类,是尽可能地成为真正的人。他们都是按照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来设计的。他们的宽容无私、自我牺牲完全发自内心,这样的境界是人类本身从未达到的。与此同时,人类自己却在忙于不择手段地将自身参数不断“提升”、优化,为此不惜损害环境、自我欺骗。在《克拉拉与太阳》里,得到提升却差点搭上性命的乔西曾向母亲表示,尽管身体弱不禁风,但她并不后悔接受了提升,而错过了提升的里克与母亲却为当年的决定后悔不迭。当机器人(自以为)在追求人性化、人格化、理想化的时候,人类自身却在非人化、机器化——我们拨开石黑一雄温柔的言辞,看到的正是这样绝妙的、强有力的反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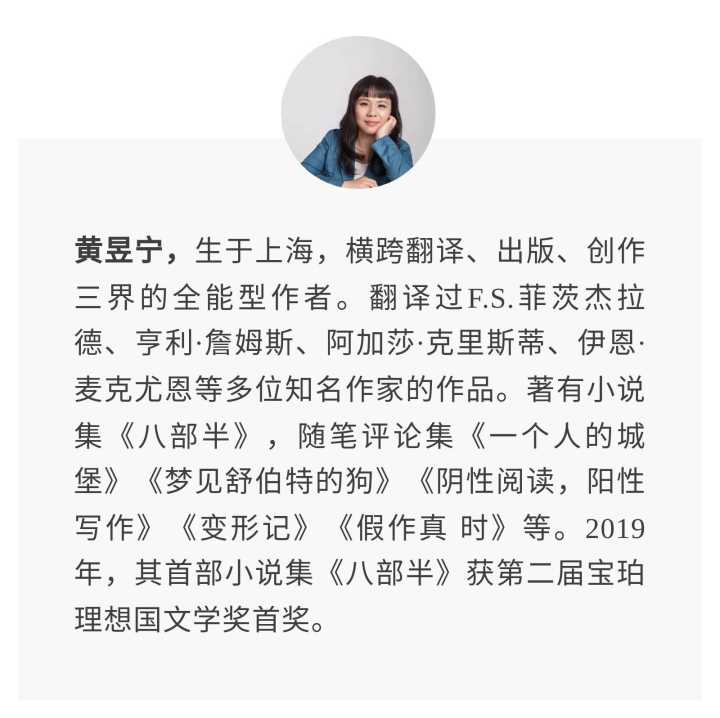
联系人:上海谷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手机:021-54039341
电话:021-54039341
邮箱:youjianbookstore@126.com
地址: 上海市凯旋都市花园2座